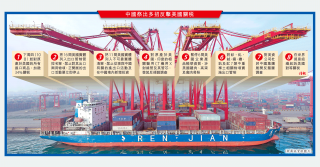2002年,在訪問約旦河西岸拉姆安拉(Ramallah)期間,諾貝爾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將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眾的生活條件,比作奧斯維辛集中營對猶太人的滅絕。上述非比尋常的言論,引發了國際社會的騷動,但薩拉馬戈堅持認為,身為知識份子,他有責任「進行情感化的類比,使人們在震驚之餘能夠深刻理解」。
薩拉馬戈絕非第一個(肯定也不是最後一個),援引納粹德國徹底消滅猶太人的圖謀,以譴責猶太國家所作所為的人。在1961年出版的著作歷史研究的最後一卷中,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認為,借助猶太復國主義,「西方猶太人以最不幸的形式,認同了非猶太的西方文明。他們已經全盤接納了西方的民族主義和殖民行為。」在湯因比看來,「沒收90萬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房屋、土地和財產」,在道德層面「等同於過去四、五個世紀西歐非猶太裔征服者和海外殖民者所犯下的最嚴重和最不公平的罪行」。
上述每一種說法都十分荒謬:將非猶太裔西方罪行等同於「非猶太裔西方文明」;暗示移民到以色列的多數歐洲猶太人都是民族主義者、征服者和殖民者,而非因大屠殺和種族滅絕而流離失所的難民;以及試圖在奪取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財產——無論這種行為多應得到譴責——與西方殖民者對非西方民眾的極端暴力間實現道德上的對等。人們只能希望湯因比沒有包含納粹德國的罪行。
儘管人類歷史充滿了大規模謀殺,但納粹基於怪誕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圖謀剷除整個民族的做法,仍然無與倫比。無論是出於惡意抑或是純粹的無知,將納粹暴行與其他形式的暴力相比都不僅錯誤,而且具有破壞性,美國國會議員大衞森(Warren Davidson)將新冠疫苗強制注射令,比作大屠殺就是這方面的實例。上述比較無一例外地扭曲了我們對時事的理解,同時,也淡化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對於猶太人所犯下的暴行。
但有人再次利用上文提到的大屠殺,來類比形容加沙正在發生的悲劇性事件。在與德國總理肖爾茨(Olaf Scholz)舉行的聯合新聞發布會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將哈馬斯稱為「新納粹」。他表示,「我們正在目睹的加沙哈馬斯殺人犯野蠻行徑,是自大屠殺以來針對猶太人所犯下的最嚴重罪行。」
內塔尼亞胡的言論,無疑反映了許多以色列人的觀點。我曾聽到一位批評內塔尼亞胡的以色列人表示,目前的局勢就像1940年,針對哈馬斯的戰爭,其實是一場必須通過「徹底消滅」敵人來贏得勝利的「反邪惡之戰」。但哈馬斯在10月7日對逾1400名以色列人的恐怖屠殺,其規模更像是一次針對猶太人的殘酷殺戮,而不是近乎徹底滅絕歐洲猶太人。
以色列人對哈馬斯的惡意襲擊深感震驚十分自然。以色列成立的主要動機是為猶太人創造安全的避難所,同時保障曾面臨數百年迫害的猶太少數民族的安全。保護猶太人免遭屠殺一直是內塔尼亞胡呼籲的核心。以色列作為反第二次大屠殺堡壘的說法,曾被幾代以色列領導人所援引。
巴勒斯坦人則不得不因猶太人在自己國家獲得安全感的願望而遭受苦難,這是一個悲劇,現代以色列國父賓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早在1919年就已經預言。在英國政府宣布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民民族家園」僅短短兩年後,賓古里安便預見到,「實際不存在任何解決方案。我們希望巴勒斯坦歸屬於我們民族,而阿拉伯人則希望歸屬於他們。我不知道怎麼樣的阿拉伯人才會同意,允許巴勒斯坦歸屬於猶太人。」
自那以後,雙方均曾出現大量的暴力、誤判和惡意行為。就像此前的賓古里安一樣,內塔尼亞胡相信衝突無法解決,只能控制。通過在巴勒斯坦人中製造政治分歧、擴大約旦河西岸猶太定居點,並在加沙定期發動軍事進攻,內塔尼亞胡認為,他可以保持對巴勒斯坦人的控制,並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儘管該策略遭遇了慘重的失敗,但將以色列政府的所作所為與納粹德國相提並論,無疑既不符合實際,而且幾乎始終如一地秉持反猶太思維。
與此同時,更糟的是,以色列領導人始終堅持將針對哈馬斯的戰爭,視為善與惡之間的一場生存之戰。邪惡屬於形而上學,而非政治概念。正如賓古里安本人所說,以巴爭端需要政治解決,因為雙方衝突本質上關乎土地和主權。
但只要以色列領袖在每次巴勒斯坦敵對行動後都只看到奧斯維辛之門,便不可能有任何解決方案。剩下的只有徹頭徹尾的主宰。
對巴勒斯坦人而言也是如此。只要以色列人被視為邪惡的「定居殖民者」並被比喻為納粹,那麼,像10月7日那樣的恐怖襲擊,就會被稱讚為英勇且必要的抵抗行為。就目前來看,政治解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恐怖暴力和殘酷報復,啟動了令人痛苦而難忘的循環。但如果將之視為一場反邪惡之戰,那麼政治解決將成為不可能。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3.
www.project-syndicat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