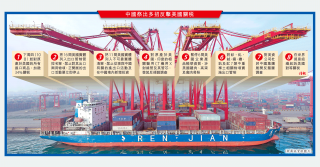根據今年3月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項調查,61%的美國人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墮胎應該是合法的。即使如此,美國最高法院還是推翻了1973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判決中確立的憲法墮胎權。
難怪反應如此激烈。民主黨女議員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呼籲彈劾兩名最高法院法官,因為他們在參議院確認聽證會宣誓時撒謊。驚慌失措的評論員警告美國民主的終結。其他人指摘厭女症和「劇場陽剛之氣」。
美國墮胎辯論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很少受到關注:在美國公共生活中,一股極度保守的天主教勢力在穩步上升。當然,天主教徒在許多問題上的分歧不亞於其他任何人,包括墮胎權。自由派天主教徒,例如總統拜登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以及投票給民主黨的大約50%的天主教徒中的許多人,都支持憲法規定的墮胎權。最高法院3位自由派之一的大法官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也是如此。但9位大法官中有5位堅持天主教的極端保守路線,認為即使是胚胎也有靈魂,因此神聖不可侵犯。
撰寫推翻「羅訴韋德案」裁定多數意見的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引用了十七世紀的英國法學家黑爾(Matthew Hale),他認為墮胎是謀殺(他也相信女巫)。這種觀點與當代美國生活的主流相去甚遠。但激進的天主教徒——他們就是這樣——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反墮胎運動背後的推動力。
即使是保守的新教徒,當時也支持「羅訴韋德案」的裁決。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在 1973年指出,「宗教自由、人類平等和正義,因為最高法院的墮胎裁定而受到推動。」但十年後,福音派保守派擔心,進步世俗主義浪潮會威脅種族隔離的基督教院校這樣的寶貴機構,開始與激進天主教徒朝着相同的目標。「羅訴韋德案」成了他們的滙聚點。他們的共同目標是打破由憲法制定者精心豎立的政教分離之牆。
一些激進分子現在甚至聲稱,政教分離從來不是真正的意圖。用極右翼共和黨女議員貝伯特(Lauren Boebert)的話來說:「我厭倦了這種憲法根本不存在的政教分離垃圾。」
但事情進展很快。在推翻「羅訴韋德案」幾天後,最高法院決定華盛頓州的一名足球教練,有權在他的公立高中舉行賽後祈禱會。這也打破了禁止學校等公共機構,行使作為私人事務的宗教表達先例。
激進分子呼籲「宗教自由」。如果一名足球教練想在足球比賽上祈禱,而周圍的球員可能不想引起他的反對,那麼他只是在行使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的權利。
但政教分離,至少在美國等大多數新教民主國家,恰好是為了捍衞宗教自由。法國的laicité概念,旨在防止天主教神職人員干涉公共事務,而美國憲法旨在保護宗教權威免受國家干預,反之亦然。
直到不久前,美國新教精英還對天主教徒持懷疑態度,除了勢利的反愛爾蘭或反意大利情緒外,一個原因是擔心天主教徒會更忠於他們的信仰,從而更忠於梵蒂岡的權威,而不是忠於美國憲法。這就是為什麼在1960年甘迺迪競選總統時,不得不強調他堅信「在一個絕對政教分離的美國,不會存在天主教主教會指示總統(如果他是天主教徒)如何行動的事情……」
新教精英所擔心的,現在成了一個真正的威脅。天主教激進分子和新教狂熱分子,正在積極嘗試將他們的宗教信仰,強加於公共領域。阿利托和其他天主教徒,如前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將世俗主義視為(用巴爾的話)對「傳統道德秩序」的威脅。他的意思是,對基督教道德秩序的嚴格解釋。根據阿利托的說法,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間的神聖制度」。有一天——可能很快——他可能會決定,推翻最高法院於7年前承認聯邦同性婚姻的權利的裁決。
將宗教議程注入政治或法律的危險,遠不止於侵蝕世俗機構的自主性。它使理性的政治辯論變得不可能。當然,政治不會脫離價值觀。政治家乃至法學家認為,宗教價值觀很重要並沒有錯。但是當宗教正統勝過所有其他考慮時,就會出現一個嚴重的問題。
以色列哲學家瑪律加利特(Avishai Margalit) 在他的《論妥協與腐朽的妥協》(On Compromise and Rotten Compromises)一書中,簡潔地描述了這一點。在「作為經濟的政治」中,物質利益是「可以討價還價的,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而在以神聖為中心的宗教圖景中,神聖是不可商量的」。
因此,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政治目前處於如此危機的狀態。愈來愈多的世俗左派和宗教右派捲入了一場文化戰爭,圍繞着性、性別和種族展開,政治不再可協商。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制度開始瓦解,魅力煽動和暴力政治的舞台準備就緒。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